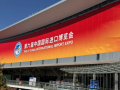东方医药网获悉今年3月,哈医大一附院杀医案发生后,国内又连续发生几起患者伤害医生事件,而乌鲁木齐也发生了两起患者家属殴打医生事件。针对频频出现的袭医现象,卫生部上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二级以上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协调设立警务室,这些都将医疗机构推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身陷危机公关的漩涡中。一时间,全国各地针对医疗机构应对舆论危机的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6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办的“医院首席新闻官培训班暨中国医院院长危机公关高峰论坛”上,就我国现阶段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医疗改革中怎样修正医患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记者独家专访了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副总编辑、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赵安平,《中国医药导报》杂志社、《中国当代医药》杂志社副总编刘志学。
赵安平和刘志学认为,加强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重塑社会公信力,才是医患关系走向和谐之道。
记者:哈医大一附院事件发生后网上出现两种对立的声音,一种站在患者角度、一种站在医生角度,您既熟悉新闻行业又熟悉医疗行业,是站在医患关系这根杠杆“黄金分割点”上的人,您如何看待最近陆续发生的患者伤害医生事件?
赵安平:我既是医生的家属(妻子是医生),又是患者的家属(父亲患脑中风12年)。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没有考虑过角色意识,考察评价这一问题更多的是以一个“人”的标准出发,从一个基本的人的角度来看,砍杀谁也是不能容忍的。
最近发生的几起患者伤害医生事件,实际上是发生在医疗机构的刑事案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医患纠纷、医患矛盾引起的。现在人们看病为什么热衷于找熟人?是因为中国社会信任度下降。现代社会主要是和陌生人打交道,靠的是建立一套大家都遵守的信任体系和规范。但如今看来,我们的信任系统出现了漏洞和缺失。
记者:据一家医学专业网站统计,仅去年全国就发生10起伤害医生案件,甚至发生哈医大一附院事件后,有八成网民投票时选择了“高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刘志学:我想应该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改革开放后,在抓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忽略了道德建设,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反映到医患关系上,就是这种诚信体系的崩溃。另一个方面是,现代媒体的发展能够把消息及时、迅速、广泛地传播出去,再加上网络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发布信息的平台,推波助澜,使医生的形象受到曲解。
从更深层次来看,我国的医改虽然已取得重要进展,医疗保险体系初步建立,但当前医疗保障水平仍较低,病人看病自费比例较高,遇大病、复杂疾病时难以承受巨大的医疗开支,有的人为了交医疗费甚至卖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病人死亡了,人财两空,对家属的打击是巨大的。家属对死亡不理解或想从医院获得一定的赔偿,是造成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医患之间认知的差距。尽管当代临床医学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有很大局限性。医生不是神仙,不能包治百病。而公众对医疗技术期望值过高,医生与患者家属沟通不够,未能让患方充分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及疾病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当病人发生未预料到的情况时,不能理解,从而产生纠纷。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导致了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
记者:这些事件后,包括新疆在内的全国很多医院都很紧张,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全国各地针对医院该如何应对舆情危机的培训班犹如“及时雨”,这是医院危机意识在悄悄觉醒吗?
赵安平:不管是全国还是新疆,出于安全需要的防范是必要的,但能有多大的效果?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
刘志学:出现这种现状,说明医疗机构已经无路可走了,以至于设立警务室、戴钢盔上班。医疗机构本来是治病救人的,现在自己却受到威胁。作为医生来讲,你觉醒后怎么办?是现实逼着你去认识,还是自觉意识?和谐医患关系不仅是医患双方,根源还在于整个社会公民素质的提高,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
赵安平:医院不光是危机公关,医院与社会的融合度与共振度、达成社会价值共识方面需要提高。医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机构,医生是最有主观能动性的一个职业,自信度很高,这限制了他和患者的正常沟通,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他需要患者,而且需要和患者好好沟通。我有个朋友给孩子开药,他对医生说:“开青霉素吧,别开先锋了,青霉素便宜”,结果这个医生张口就说,“地瓜便宜,能治病吗?”你能说医生说得不对吗,但是医生沟通的对吗?
现在有种医学叫做叙事医学,就是说在治疗过程中怎么和病人沟通。对医生的作用评价现在是3个:偶尔能治愈、常常去沟通、总是去安慰,这是美国的一个医生去世后在他的墓志铭上写的。医生的作用中,只有1/3是治病,其余的三分之二是沟通和安慰。医生应该成为一个公共关系的专家,现在缺这块,我觉得就是大问题。我做过那么多医疗新闻报道后有个感悟:医生不仅是在救命还是在救人,救人救的是人心。
记者:您是报道河南上蔡文楼艾滋病疫情的首批记者之一。当时著名的桂希恩教授是在当地患者家属的保护下做了很多工作,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医患携手共同对付疾病。而现在是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还是两代人的从医理念不同了?
刘志学:从两院院士到各医学学科的老专家,我采访过200多人。在工作中,我感受到的老专家身上的那种敬业精神、悲悯情怀非常重要。和他们对话,你能非常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比如著名临床肿瘤学家孙燕院士,对病人能拿出三到四套诊治方案,并详细询问病人的家庭经济情况,以酌情施治。从他们这一代老专家身上,可以看到我们传统的医德建设。现在的年轻医生在这方面很欠缺,我们可以从根源上找一下。学生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整个教育过程中缺失了什么?在这个教育链条中,不仅仅是医生这个执业群体的传统道德教育有问题,而且自私、自我是70后、80后、90后身上最明显的特点,反映到职业生涯上也是一样,这就是这一代人的医德不那么完善的根源。
记者:医疗机构要想改变现状,能不能主动做点什么?
赵安平:这个问题很复杂,医疗机构是个口,很多社会矛盾在这里爆发,到底是不是它的问题?不能说它没有问题,但是也不能全部把问题归结到医生身上。这次杀医案发生后,卫生部的表态有个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过去反复强调要多沟通,而且医生是沟通的主动方,这次说根本上要靠医改来解决,这一点我认为是个很大的进步。
刘志学:医院作为一个社会单元,如果院长有眼光应该先从医德抓起,可以先从内部改变。医德的内涵包括很多,技术素质、职业要求、个人修养等。比如说可以从很简单的两件事情先着手:不拿红包、不收回扣。我总体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合情合理地去提高医疗机构的美誉度、知名度,这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缓和医患关系的行为。
记者:医疗体制的不完善对这些现象是不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东方医药网刘志学: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医疗体制的大框架实际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比如说新医改5项重要内容之一的医药分家,很难做到。为什么呢?就是体制原因。我们国家医生的诊断费没法和欧洲比,人家完全可以靠医事服务费,但我们现在调整一下医疗费试试,首先是患者不答应。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遗留下来的惯性因素,要改变不是几个部委制定一个医改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政策都是好的,问题是执行这种政策的社会环境允许不允许。
记者: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怎么才能修正医患关系,达到相对的和谐?
刘志学:我觉得目前连提这个问题的基础条件都不具备,你怎么修正?我们的道德在滑坡,老太太摔倒没人敢扶,再比如“小悦悦事件”,光医生单方面提高素质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没事则好,一旦遇到患者曲解你,你的委屈就越大,在以后的工作中情绪反弹就越大,可能对患者更不好了。
赵安平:规范。一切照着规范去做。发生纠纷,有规范的渠道,有令人信服的、让大家都能认可的有公信力的仲裁机构。现在主要问题是处在一个转型期,转型期的特点是旧的没了,新的还没出来,成长的烦恼。我们要尽快缩短这种过程,但是要完全避免是不现实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当今社会最容易被点燃的情绪是愤怒,事实上,医患之间对立没有赢家,是让它走向对立和撕裂,还是走向和谐和共振,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另外,在公信力的建设上还要努力,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可能努力了9次,有一次没努力好就全塌了,但当建立起来后,要塌也不容易。
东方医药网记者:在新医改的各项措施中,您认为哪些有助于缓和医患关系?
刘志学:目前,医患关系有朝着恶性方向发展的趋势,哪怕是一个医生派一个警卫保护,我个人见解在短时间内这种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为什么呢?医院建立警卫室又给患者造成了紧张心理,患者对医院的戒备会更高,导致了恶性循环。
最根本原因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崩溃。反映到医患关系上,就是医生和患者互不信任,没看病,先取证,做手术要全程录像等的现象。先不讲病能不能治好,实际上就是先为打官司做好准备。医疗消费是强制消费,生病了无论有钱没钱都得到医院去治,它是被动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又对医生信不过,只好先防备。最早是复印病历,后来发展到手术全程录像,再发展到从第一次看病就拿出手机录音……逐渐逐渐一层层叠加,导致医患之间成了对峙关系。现在医生、患者和疾病之间成了互为矛盾的三角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不从各个方面加强道德体系的建设,医患和谐是个很难实现的话题。